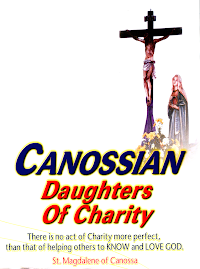白白領受、白白付出
蘇莉芳修女
我的父母和六個兄弟是我生命中力量的泉源。小時候他們曾貼心的保護我和疼惜我,讓我在快樂中長大;加入修會後的四十年歲月中,他們仍在精神上和心靈上支持我。
1952年我七歲,就讀檳州北海中華公學(華校)。由於家中只有我是女孩,媽媽很希望我轉到聖嬰會修女辦的小學/中學,以便接受完整的教育和適當的宗教輔導。但那間修道院學校是英校,名望很高,幸虧有胡余生舅舅的協助,才如願的轉過去就讀小三。媽媽在娘家排行老大,外公是個很虔誠的教友,他在媽媽出嫁時就萬般叮嚀說無論多麼的艱辛,都必須把天主教信仰傳給下一代,以盡到教友家長的本分。由於北海的華小並非教會學校,所以媽媽就請一位女傳道員(道理姑)每星期來家裡教要理。信仰堅定的媽媽和工作勤奮的爸爸在小孩的成長時期就為我們打下穩固的基礎。
1963年底我高中畢業,暫時在母校當臨時教員。少年的我忙著趕流行;年輕人的各種娛樂如唱歌、跳舞、郊遊、開派對、交朋友、買衣服,我都很有興趣。媽媽對活力充沛的我設下一個條件:只能參與堂區團體舉辦的活動。我對北海堂區活動很熱衷,幾乎把教會當成第二個家。那時有幾位熱愛音樂的教友(三個吉他手和一個鼓手)成立了「夜桂濃」(The Equinox)樂隊,找我當主唱。我們常在母校的音樂會和聖堂的善慈會中義演,默契十足。有一回,北海戲院為The Young Ones電影(由Cliff Richard主演)做宣傳,特辦了一次樂隊歌唱比賽。「夜桂濃」勇敢的跨出教會去參賽,結果竟抱回冠軍!那凱旋的一天真令人難忘啊!
可惜美好的日子總是短暫的;樂隊成員為了各自的學業必須勞燕分飛,「夜桂濃」也難逃解散的命運。那時我首次問自己:「我的生命到底在追求甚麼?為何每次活動結束後都會感到很空虛?有甚麼東西可以永遠滿足我的嗎?」。當世俗的干擾平息時,天主的召喚就在祈禱的寧靜中彰現;祂行動了。
有一天,道理姑忽然問我:「你要去當修女嗎?」
「我?當修女?」她不是在開玩笑吧?
我從未有過這個念頭!修女的生活那麼神聖,我可配不上……;何況要犧牲這麼多的東西……,腦袋即刻升起一堆藉口。震驚的我無法答覆她,但這問題卻一直懸在心上。我可以選擇繼續擁有各種物質的享受,但我知道它們都無法安頓我的心;我的心唯有在服務他人時才能在主內安憩。加入修會,跟隨耶穌去服務祂的子民,我就可以把祂賜予我的所有美好東西,交還給祂。於是我決定去嚐試一下。
天主藉著道理姑來點醒我,挑戰我去做各種犧牲。首先我必須離開雙親、兄弟們和溫暖的窩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修院生活是怎樣的?必須常常祈禱嗎?必須不斷付出嗎?接著又想到從此不能再穿上喜愛的流行服飾、不能再跟玩伴出遊了………,進修院會像進監牢一樣糟糕嗎?這些怪異的問題排山倒海而來。但我緊緊依偎天主,深信祂如果給了我聖召,就一定會協助我的。可是要我放棄那麼多物質的享受,我會很難過。於是我向主祈禱:「主啊!祢是我生命的摯友,請來與我同行吧!」
1966年我終於決定進入嘉諾撒修會在新加坡的保守生修院。原本以為當修女很豪邁,但要跟父母和兄弟們告別時,卻感到無比沉痛,因為不知何時能再見到他們;我唯有將一切都托付給慈祥的天主。雖然我在新加坡暫時不能跟遠在天邊的家人見面,但我卻強烈的感覺到父母祈禱的力量。1969年初,我在新加坡修院宣發修女初願。看到闊別三年的父母,讓我十分感動,天主的恩寵實現了這一切。
1976年9月,我回到北海聖堂宣發終身願,由主教和多位神父主持彌撒,不少的親友和不同修會的修士修女都來參與盛會。從那天起,我就是正式的修女了;如今回想起來仍感到無比的興奮和光榮。不管未來是好是壞,我都會一直往前走,只有天主才是我生活的重心。我的父母認為孩子是天主暫借給他們的,如果祂召叫孩子去為祂服務,他們當然要全心全力去配合。為主服務就是去照顧那些不幸的小孩、貧苦的人、生病的人和無家可歸的老人。在照顧他們時,我就是對主說:「謝謝!」
我所擁有的許多美好事物,都是白白領受,如今當然也可以不求回報的付出;就好像我的父母從天主那裡白白的領受了我,又白白的把我付出一樣。然而,我們若往深層去想,為主做犧牲絕對不會是「白白的付出」,因為在張開雙手付出的同時,主必然會填滿我們的雙手。這是一個多麼美妙的真理啊!
蘇莉芳修女
我的父母和六個兄弟是我生命中力量的泉源。小時候他們曾貼心的保護我和疼惜我,讓我在快樂中長大;加入修會後的四十年歲月中,他們仍在精神上和心靈上支持我。
1952年我七歲,就讀檳州北海中華公學(華校)。由於家中只有我是女孩,媽媽很希望我轉到聖嬰會修女辦的小學/中學,以便接受完整的教育和適當的宗教輔導。但那間修道院學校是英校,名望很高,幸虧有胡余生舅舅的協助,才如願的轉過去就讀小三。媽媽在娘家排行老大,外公是個很虔誠的教友,他在媽媽出嫁時就萬般叮嚀說無論多麼的艱辛,都必須把天主教信仰傳給下一代,以盡到教友家長的本分。由於北海的華小並非教會學校,所以媽媽就請一位女傳道員(道理姑)每星期來家裡教要理。信仰堅定的媽媽和工作勤奮的爸爸在小孩的成長時期就為我們打下穩固的基礎。
1963年底我高中畢業,暫時在母校當臨時教員。少年的我忙著趕流行;年輕人的各種娛樂如唱歌、跳舞、郊遊、開派對、交朋友、買衣服,我都很有興趣。媽媽對活力充沛的我設下一個條件:只能參與堂區團體舉辦的活動。我對北海堂區活動很熱衷,幾乎把教會當成第二個家。那時有幾位熱愛音樂的教友(三個吉他手和一個鼓手)成立了「夜桂濃」(The Equinox)樂隊,找我當主唱。我們常在母校的音樂會和聖堂的善慈會中義演,默契十足。有一回,北海戲院為The Young Ones電影(由Cliff Richard主演)做宣傳,特辦了一次樂隊歌唱比賽。「夜桂濃」勇敢的跨出教會去參賽,結果竟抱回冠軍!那凱旋的一天真令人難忘啊!
可惜美好的日子總是短暫的;樂隊成員為了各自的學業必須勞燕分飛,「夜桂濃」也難逃解散的命運。那時我首次問自己:「我的生命到底在追求甚麼?為何每次活動結束後都會感到很空虛?有甚麼東西可以永遠滿足我的嗎?」。當世俗的干擾平息時,天主的召喚就在祈禱的寧靜中彰現;祂行動了。
有一天,道理姑忽然問我:「你要去當修女嗎?」
「我?當修女?」她不是在開玩笑吧?
我從未有過這個念頭!修女的生活那麼神聖,我可配不上……;何況要犧牲這麼多的東西……,腦袋即刻升起一堆藉口。震驚的我無法答覆她,但這問題卻一直懸在心上。我可以選擇繼續擁有各種物質的享受,但我知道它們都無法安頓我的心;我的心唯有在服務他人時才能在主內安憩。加入修會,跟隨耶穌去服務祂的子民,我就可以把祂賜予我的所有美好東西,交還給祂。於是我決定去嚐試一下。
天主藉著道理姑來點醒我,挑戰我去做各種犧牲。首先我必須離開雙親、兄弟們和溫暖的窩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修院生活是怎樣的?必須常常祈禱嗎?必須不斷付出嗎?接著又想到從此不能再穿上喜愛的流行服飾、不能再跟玩伴出遊了………,進修院會像進監牢一樣糟糕嗎?這些怪異的問題排山倒海而來。但我緊緊依偎天主,深信祂如果給了我聖召,就一定會協助我的。可是要我放棄那麼多物質的享受,我會很難過。於是我向主祈禱:「主啊!祢是我生命的摯友,請來與我同行吧!」
1966年我終於決定進入嘉諾撒修會在新加坡的保守生修院。原本以為當修女很豪邁,但要跟父母和兄弟們告別時,卻感到無比沉痛,因為不知何時能再見到他們;我唯有將一切都托付給慈祥的天主。雖然我在新加坡暫時不能跟遠在天邊的家人見面,但我卻強烈的感覺到父母祈禱的力量。1969年初,我在新加坡修院宣發修女初願。看到闊別三年的父母,讓我十分感動,天主的恩寵實現了這一切。
1976年9月,我回到北海聖堂宣發終身願,由主教和多位神父主持彌撒,不少的親友和不同修會的修士修女都來參與盛會。從那天起,我就是正式的修女了;如今回想起來仍感到無比的興奮和光榮。不管未來是好是壞,我都會一直往前走,只有天主才是我生活的重心。我的父母認為孩子是天主暫借給他們的,如果祂召叫孩子去為祂服務,他們當然要全心全力去配合。為主服務就是去照顧那些不幸的小孩、貧苦的人、生病的人和無家可歸的老人。在照顧他們時,我就是對主說:「謝謝!」
我所擁有的許多美好事物,都是白白領受,如今當然也可以不求回報的付出;就好像我的父母從天主那裡白白的領受了我,又白白的把我付出一樣。然而,我們若往深層去想,為主做犧牲絕對不會是「白白的付出」,因為在張開雙手付出的同時,主必然會填滿我們的雙手。這是一個多麼美妙的真理啊!